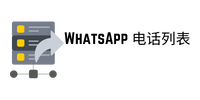具体治疗的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仅仅是描述性的,或结构性的,假设它在其所有自身的模态中都是如此,或仅仅是相对的,与经典分析治疗相比,是相对的。有一个简单的描述形式:治疗持续时间不长,且持续时间是固定的。在IPA中,已经定义了简短疗法 殊治疗 。短期心理治疗。
然后,我们意识到,自巴林特和奥恩斯坦以来,我们常常更喜欢谈论一种稀有鸟类:“开发一种可以定义和改进的简短、系统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形式?[1] » 如今,人们的担忧恰恰在于此种做法所隐含的风险,我们扪心自问:“短期疗法如果被纳入管理式医疗行业,将会带来危险[2] ”
相反,最近这位作者指出,这些疗法中的大多数专家都更加关注受试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治疗过程中的关系,而不是受试者自身发生的事情。研究“关系”涉及考察语言:“我们的习语就是我们的奥秘。 [3] » 这句话适用于病人和治疗师…特异性与精神分析的传播方法以及将其“固定”在模型中的尝试是分不开的,无论模型有多小。我们知道,对于“先驱”作者来说,这意味着一种超越,一种时间的限制,也就是说,一个限制性目标的定义,著名的“治疗重点”。然而,所谓的“焦点冲突”仍然是幼稚的“核冲突”的化身,而这些冲突本身被弗伦奇定义为冲动的。然后争论就开始了:我们应该选择病人吗?选择可以部分定义特异性本身,但对这些模式的不同意见并未产生稳定的定义。
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人们常常忘记,最初治疗标准并不是最重要的,而研究患者和治疗师之间的互动才是最重要的。这就要求从患者的角度和分析师的角度尽可能准确地报告该过程。简短的时间使得互动和干预得以充分进行。而弗洛伊德则恰恰相反,他认为分析的开始和结束只适合报告与治疗过程相关的情况,而治疗过程则更难解释。
费伦齐之后 殊治疗 的另一种倾向是
认为这种治疗形式有可能激活特定的过程。弗洛伊德曾回复费伦齐:“但无论这种流行心理疗法的形式和要素如何,最重要的、最活跃的部分仍将是那些从严格的精神分析中借鉴而来的、没有任何偏见的部分。 [4] » 20世纪40年代,亚历山大决定通过改变节奏、中断治疗或对移情情况采取相反的方法来激活移情。例如,如今有些人会故意激发焦虑。
通过在2005年在巴塞罗那使用“快速治 WhatsApp 号码数据 疗”这个术语,我们选择强调节奏而不是持续时间的问题,这种节奏会赋予治疗风格。 J.-A. Miller 强调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只知道长期分析治疗才能迅速见效。问:我们能在精神分析中定义类似快速治疗的东西吗? [5] » 经典治疗的关键时刻往往表现为快速时刻,可以作为快速治疗的灵感。从快速处理的角度来看,转移的位置在哪里?简洁性使得重复的展开几乎没有空间。但另一方面,难道不存在一些基本要 Dusty 开始涉足 素在转移的维度上显露出来,因而需要关注作为症状的“关系”吗?巴林特在互动中寻找的也是这些自发的、快速的转移效应,而不是以重复的形式出现。拉康还向我们表明,转移并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再现,而是新现实的产生。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限制
的是时间还是目标,目标本身必须被定义,而在精神分析中它似乎是不确定的?但这种看似不确定的东西本身就被高定义地理解为分析师及其欲望的分析……拉康恰恰将分析师的欲望置于转移的中心。在这个级别上,没有分析师会授权他的“应用”执行这项任务!我们注意到,许多治疗都采用单一形式,这与“框架”无关,而与分析师的行为因时间、其决策的“焦点”或其愿望而受到的调节有关。短期治疗和治愈的共同点在于,终止治疗可以决定他们的存在。 J.-A.米勒在巴塞罗那 印度号码 强调道:“拉康认为分析确实会结束。这些案例很有价值,因为它们证明了实验的有限性,即使它只是一个循环。人们总是可以进行更多轮次,但是每次循环的体验都有其完整性。这将是一个新的论点:分析是如此的可终止,以致于它会结束好几次(笑),它喜欢结束,并且重复结束。这与经验紧密相关。有一个最终的结局,并且正如分析喜欢结束的那样,它再次结束了。也就是说,它迫使你重新开始——以便完成。[6] »
我们常常看到,受试者本人或分析师可以决定将结束一词放在固定内容之前。那么,这是仓促、谨慎,还是死路一条?在这种快速的逮捕行动中,分析师和他的愿望扮演了什么角色?这很容易被归咎于病人,还是行政部门?
P.-G.盖根在巴塞罗那这样评论这一结局:“这并不是说病人已经用尽了分析治疗能为他提供的所有资源,而只是因为所获得的最佳资源并没有迫使他进一步投入。 [7] » 他从中看到了自由。但我们也发现,这种快速治疗通常(并非总是)只是作为分析的初步手段。这并不意味着它正是初步治疗。